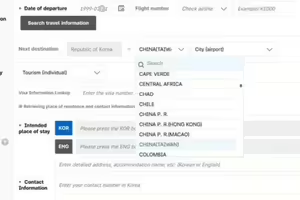陰魂不散的「表哥」
曾德來又向我借錢,數目不大也不小,塊。
方明皺了皺眉,還是把銀行卡丟給我。
曾德來是我的遠房表哥,住在距我們千里之外的城市。他有殘疾,歲那年,為了把當時才歲的我從一幢快要垮掉的房子里救出來,他的腿被掉下來的屋樑砸中。我欠了曾德來的,所以必須還。
與方明結婚不到一年,加上這次,曾德來管我借過次錢。上一次借錢時,方明有些生氣,直到我把緣由告訴他,他才大度地表示「借吧」。可是,曾德來向我索要錢財的次數過於頻繁,方明有理由不開心。
我亦覺得很羞恥。曾德來每次打來電話,我都覺得對不起方明,唯有在別的方面補償他,比如更精心地煲湯、更仔細地熨燙他的襯衣、在床上努力搞點兒花樣。除此之外,我對於現狀無能為力。
今年月,曾德來要求我去看他。我對方明說,因為殘疾,曾德來一直獨身,今年又添了病,好像是哮喘。發作的時候,身邊連個端茶遞水的人都沒有。方明便讓我去了。
可是,我騙了方明。曾德來沒有殘疾,他是個歲出頭的健壯青年。甚至,他根本就不是我的遠房表哥。我是在歲那年認識曾德來的,那時他與我在同一家公司。年紀相仿、相貌相當,我們順理成章地談起了戀愛。歲女孩的愛情,自然拙樸又激烈。我不知道,更不敢相信,曾德來會一邊與我談戀愛,一邊當著老闆娘的情人。
那時候的我多年輕啊!發現曾德來腳踩兩條船後,我的第一反應不是憤然離開,而是把他們的姦情寫成郵件,匿名發到老闆的郵箱裡。
接下來,老闆娘羞憤之下跳樓自殺。
曾德來告訴我,老闆娘死後,老闆揚言要找出寫郵件的人,給他老婆報仇。老闆在那個城市很有背景,黑道白道都有人,他說到的事一定做得到。曾德來答應會保護我,不讓老闆知道寫郵件的人是我。但我還是很害怕,不久就和曾德來分手,遠離了那個城市。
但,分手後的曾德來忽然變得很難纏。他沒有錢時,就向我要錢;沒有性伴侶時,就要求我飛回去陪他。我不敢反抗,因為他每次都會提到那個死不瞑目的老闆娘。他說老闆一直沒有再娶,發誓要手刃仇人。直到他總算結了婚,才不再讓我陪他睡覺。可他要錢的那隻手還是沒有停止伸向我,因為他一直沒有正經工作,時時手緊。
曾德來結婚後,我才敢結婚,以為總算是風平浪靜了。沒想到,他會再次召喚我「陪床」。
買一個安寧有多難
曾德來在人群中對我展開笑容。他長得越發得丑,像只倉鼠。我盯著他,笑不出來。
曾德來居然離婚了。他說:「我很寂寞,你有義務安慰我。」他還說:「你知不知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了,勢力也越來越廣。但他還是沒有再娶,倒是一個難得的痴情人。」
曾德來口中的「他」,自然是那個老闆。而曾德來告訴我這些的目的,不過是又一次提醒我:別心存僥倖,所有人都沒有患失憶症。
我盯著那張酷似倉鼠的臉,很是疑惑,想不通當年怎麼會愛上這樣一個人。而我這次來,並不想「安慰」他,而是想徹底解決問題。
我拿走了家裡的一張銀行卡,裡面有萬。這筆錢,方明說了不準動用,這是給未來孩子攢的教育基金。我想用這筆錢,買一個終身的安寧,可不可以?
曾德來把我送到賓館,然後,他沒有要走的意思。和我睡覺,在他看來是那麼自然的一件事。他忘了,我已經結了婚,不再是當年那個到處漂泊的女子了。
在曾德來撲過來之前,我把銀行卡舉到他眼前。我說,可不可以把那個秘密一次性買斷?曾德來狐疑地打量那張卡,沒有立刻回答我。顯然,他在算賬,是馬上擁有一筆錢划算,還是長期擁有一個提款機划算。然後,他迅速做出決定,伸手去接銀行卡。
我把手一收,說:「為了防止你不講信用,你必須留點東西在我手上。」我要曾德來錄一段與我的對話,在對話里親口承認那封郵件是他寫的,為了報復老闆娘拒絕繼續和他來往。我說:「我手裡有你的錄音,你手裡有我的錢,我們互相牽制,這樣是不是比較好?」
「這樣當然不好。」他的嘴角一扯一扯地笑了,「如果你有錄音,就可以反過來勒索我。你當我是傻子嗎?明天把萬打到我賬上,然後陪我幾天,我答應從此不再找你要錢。不然,你就等著他找你報殺妻之仇吧!」說完,曾德來陰陰地笑,把門一摔就走了。
我愣在空蕩蕩的房間里,絕望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