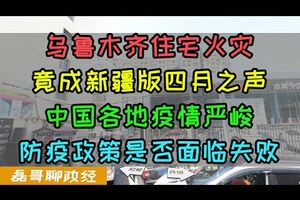裙下無匍匐的小兵,庫房沒有存貨,自己心裡頭連個可念想的人也沒有——到目前為止,我在愛情上仍然沒有任何斬獲,創造了連剩21年的紀錄。
戀還是不戀?
我身邊的人都談了戀愛。晚上,宿舍的姑娘們打電話,一片鶯聲燕語,撒嬌撒成環繞立體聲。有時放下手邊的事猥瑣地偷聽,想知道當她們談論愛情時,都說些什麼。
聽了才覺得戀愛的瑣碎無趣,無外乎是說自己一天吃了什麼,好不好吃,吃了多少,有沒有發胖的危險,胖了你是不是依然還愛著我。我對愛情剛燃燒的憧憬,往往被此打敗。
孤獨的人是可恥的,戀愛的人是傲嬌的。後者為了顯示他們掌握了某種神秘而了不得的資源,隨時隨地都可以立刻入戲做生死離別狀,暖風熏得情侶醉,只把校園做失樂園了。
大概是因為我沒愛過,也難以體會這種親密的身體接觸。所以便理直氣壯地保持著七歲女童的可笑潔癖——像小孩兒看電影時看到接吻鏡頭。
我快步走過情侶身邊,發誓自己以後不要變得像他們那樣。愛,這就是所謂愛了。我反覆咀嚼著這個字眼,覺得他們都虛頭巴腦地愛錯了。
當然,並不排除另一種可能性:愛情的好不足為外人道,暴露在外的形狀是激情、矯情和濫情,可在當事人中的版本卻是再嚴肅不過的史詩。
大概是我太苛刻了,疾惡如仇,覺得人都該戒貪戒痴,覺得只有不以耍流氓和結婚為目的的戀愛,才能稱為愛。
而我也是最近才發現,身邊的姑娘們紛紛談了戀愛,剩下單身的,卻全是些好姑娘們。
有女其姝,驚為天人,難得的是說話也爽快彪悍,總是自稱「哥」,儼然雌雄同體。有女其爽,義氣玲瓏,把周圍人照顧得滴水不漏,不過二十齣頭已上道得像摸爬滾打了很多年。她們都是單身,雖然嘴上也說徵婚徵友,可說到底,還是捨不得自己這副好身子骨。
我猜,能戀起來的條件,對方必須是你無法消化的人:要麼太遠太神太硬太強,咀嚼不動;要麼疼惜到捨不得下口,否則啊,戀愛只能是利己的過程,把對方肢解溶化變成自己的營養物,哪有什麼愛,只有吃飽後的仰頭猙獰大笑。好姑娘們的自我意識都非常強大,消化能力又強。「戀,還是不戀」似乎變成了一個「利己還是利他」的道德問題。
如果世上沒有寂寞這件事
孤獨是愛情的敵人,寂寞是愛情的朋友。
前一句好解,後一句其實也只是個故弄玄虛的文字遊戲。去情去愛,愛不了就騙了自己使勁愛,大部分原因,還是為了抗拒寂寞吧。
別人都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一家老小,生天倫之樂。有了愛情,似乎一切都順理成章。而單身的人,卻始終停留在形單影隻的「一」。「一」了許多年,便直接生了四大皆空。
所以我叫囂著要戀愛的時候,大多是受了刺激。看到七夕、聖誕別人都有約,便摔盤砸碗地發火,覺得自己奇冤無比。木心說:「人害怕寂寞,害怕到無恥的程度。換言之,人的某些無恥的行徑是由於害怕寂寞而作出來的。」每逢佳節倍思春,恐怕也是無恥行徑的一種。
我一直在做一個大膽的假設:如果世界上沒有寂寞這件事,或者,當寂寞變成有葯可醫的病,一日三次、一周一療程、一療程痊癒——寂寞消失,內心充盈,看到別人秀恩愛也不會罵髒話——如果有那樣科技昌明的一天,還會不會有人去談戀愛呢?
我在村上龍的書里見過一首極繾綣的爵士歌詞,雖然沒有聽過原唱,已酥麻不能自已:「……你不懂/愛情是什麼/直到你老到會為藍調落淚/直到你會因為失落/度過死亡忽隱忽現的夜/直到你不賭上性命就無法接吻/直到你品味含淚苦澀的唇……」
我對愛情說了許多,時而做涉世未深狀,時而又滄桑擺師太臉,分裂得連自己都無法說服。我最嚮往的,便是有人能堵住我的嘮嘮叨叨,輕蔑地說:「你不懂,愛情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