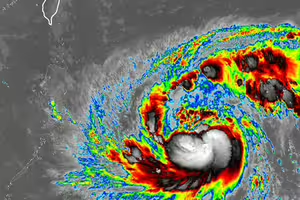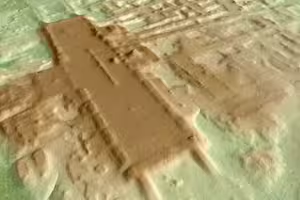一、神秘失蹤的三個女人
3月5日,「桐花」舞廳。
阿鳳是個有家有正式工作的女工,在一家服裝廠上班。服裝廠效益不太好,上班有一搭沒一搭。閑時無事,她被小姐妹拖到舞廳學會了跳舞。
阿鳳喜歡到一家名為「桐花」的舞廳跳舞,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這家舞廳離她家不近不遠,很難磁上多少熟人;二是門票適中,每次五元,能承受得了。
阿鳳每到舞場,只要一聽到或激烈或抒情的旋律,她的心跳就會加快,一種冒險的心理就溢了出來。她期待著發生點什麼,又害怕發生什麼。
3月5日,她休班,上午在家睡個懶覺,做做家務,午飯後,心裡又開始痒痒的。她修眉畫眼,卷卷頭髮,穿金戴銀,為了顯曲線,她把剛買的一身墨綠色棉絲混紡針織套裙換上,在衣鏡前上下打量,感覺十分愜意,又穿上一件淺米色真絲長風衣,娉娉裊裊出了家門。
桐花舞廳下午場的客人不多,而且多是上了年紀的。她懶得與他們共舞,推辭掉幾支曲子。等著心儀的男人出現。
正等得心裡干火火的,一個男人出現在她身邊。「能請您跳一曲嗎?」男人彬彬有禮地說完,她立即欣悅地站了起來。
那男人跳得很好。阿風曾與別的舞搭子共舞過,好與不好,她一下就感覺出來。好的舞搭子,你只需全身心放鬆,把全身心交給他,他會帶你翩翩起舞。跟上這樣的舞伴,你會倍感愉快。阿鳳有了一種預感。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她欣然迎候樂於前往。
藉著黑暗,藉著舞曲,那中年男人在阿風耳邊呢呢喃喃,講得阿鳳臉紅心跳,她怕聽又想聽。那男人說要帶她到別處坐坐,「坐」兩個時辰先給她三百元錢。阿鳳有點惱,有點怕,又有點想,總之,那男人的話好像有點吸引力,半支舞曲的工夫,那男人把三百元漲成了五百元。阿風動心了。她假裝有點不好意思地穿上風衣,低著頭跟那男人走出舞廳,就這樣神秘地失蹤了。
3月24日下午,「漱玉」舞廳。
一個叫玉蘭的無業女性閑踱到舞廳門口,腰肢扭了兩扭,幾個眼風朦朦朧朧撒出去,網到一條「魚」——一個看上去有型有款囊中有錢的男人。那男人朝玉蘭走過來。問她,跳舞嗎?玉蘭點點頭,點得很有味道。那男人主動伸出胳膊,讓玉蘭挽住,他主動買好舞票兩人雙雙走進舞廳。
也就是三支舞曲的光景,兩人又雙雙走出來,看那樣子,已很親昵,已計劃好了下一步要去哪裡要做什麼。
玉蘭心甘情願地跟上那條上鉤的「魚」走了,再也沒有回來。
4月8日下午,「桐林」舞廳。
阿英文革中初中沒畢業就去安徽農村插隊。期間,她結了兩次婚,又離了兩次婚,有一個女兒。返城後無業。阿英多數生活來源是靠出賣自己的身體。前天,她接到一封信,說她女兒在深圳因賣淫被有關部門扣下了,對方要她拿一千元錢去贖。「你怎麼與當娘的一個命啊?」阿英嘆息,「贖金一千元,還有路費和宿費,這可怎麼辦啊!」
阿英對著那張薄薄的信紙,連哭的念頭也沒有。眼淚救不了女兒,得用錢,而最快捷的掙錢路子還是自己的身體。
4月8日下午,阿英在她那暫時棲身的小屋精心化妝。她半月前把頭髮染成紅色,自己的頭髮本來泛黃,近年來,絲絲銀髮夾雜其中,看上去枯草一樣。徐娘半老的樣子,誰還要你?誰還把鈔票你?她狠狠心,於是去美髮店花一百五十元染成了紅色。
阿英畫好眼線,描好眉毛,塗好嘴唇,對著鏡子端詳,點頭又搖頭。她把所有首飾都戴上,企圖用亮金爍銀來遮掩皮膚鬆弛的老相。穿好衣服,她義無反顧地出門了。
來到桐林舞廳,當她找到目標,那個中年男人要與她那個時,她獅子大開口,要價一千元。講完她又悔,怕把那男人嚇跑。誰知那男人連眼睛也不眨一眨就答應了。於是,她跟那男人走了,從此消聲滅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