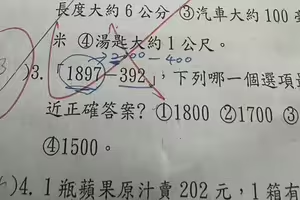他是在從鎮上回來的路上被一大群荷槍實彈的軍人抓走的,然後被強行送到一艘停在廈門碼頭的船上。幾天後,他便糊裡糊塗地隨著這艘船來到了一個他之前從不知道的地方——台灣。
因為年紀尚小,夠不上當兵的條件,到達台灣後他便被當初抓他的那幫人當成垃圾一般,一腳踹開,不聞不問。從此,他開始踏上了自生自滅的道路——四處乞討,與野貓、野狗爭奪人們倒掉的變質食物和過夜的地方。每當夜幕降臨無事可做時,他便開始想家,流著淚想回到母親的身邊。可這遙遠、迷茫得如一場白日夢,沒有人告訴他,他的家在哪裡,又怎樣才能回去。
關於故鄉的,留在他身邊,能給他溫暖和觸摸的東西很少,除了他懷中的那個用紙包起來的包裹,那是他從老家小鎮上帶來的唯一的東西。
一年後,他突然決定學習游泳,此後一直不會游泳的他,不論是酷暑還是寒冬,幾乎每天都要來到海邊游泳,先是淺水區,後是深水區,先蛙泳、潛泳,後蝶泳、仰泳。這游得越來越好,越來越遠。在他的心中有一個秘密的計劃,一個不能讓任何外人知道的計劃,關於回家的。
他整整練習了4年的游泳,一口氣已經能游很遠很遠了,此時,他覺得該將心中的那個計劃付諸實施。於是,在一個漆黑的夜裡,在茫茫夜色的掩護下,他帶著一個廢舊的輪胎,下到海里——他要游過眼前的那道長長海峽,游到日思夜想的對岸去,去見自己的母親。
可不幸的是,剛遊了幾海里,他便被台灣「海軍」發現了,巡邏隊立即將他強行從海水中撈了上來。那時的他,只穿了一條破舊的內褲,腰間卻綁著一個用塑料薄膜層層包起來的包裹。
他被台灣「法庭」以「叛國」定罪,被判15年監禁。入獄時,獄警要對他的隨時物品進行檢查,當要檢查那個包裹時,他卻死活不讓,任憑獄警對他拳打腳踢,都堅決不肯鬆手,最後逼得獄警只好無奈地搖頭作罷。在獄中時,他拚命地勤奮「改造」,設法極力討好獄警,以期望能獲得減刑的機會,早日出來。
最終他只被減了1年刑,出來後,他多次還想繼續泅水偷渡到對岸去,但由於監管森嚴,每次都無法成行。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兩岸的關係得到了緩解,他才和眾多故鄉在大陸的同胞一樣,獲得了一個回大陸探親的難得機會。
時光如電,日月如梭,一轉眼時間已經過去數年了,他不敢奢望自己還能夠見到母親,也許母親早已作古了。但讓他萬分欣喜的是,他居然真的找到了她。雖然母親早已頭髮花白、耳也聾了,眼也花了。
他雙膝跪倒在母親的面前,將那個這多年來一直寸步不離帶在身上的包裹,雙手捧送母親的面前。裡面竟是一包早已朽成粉末、變了顏色和味道的中草藥。「娘,兒子把葯給您抓回來了。」他號啕大哭,淚如雨下。
當年,他是在替母親抓藥回來的路上被人抓走的。
母親當時得的是肺癆,在那個缺醫少葯的年代,此病素有「十癆九死」之可怕後果,可母親卻意外地活了下來,「兒呀,娘這些年,一直忍著不死,就是為等你的這包葯呀。」母親顫巍巍地雙手將他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