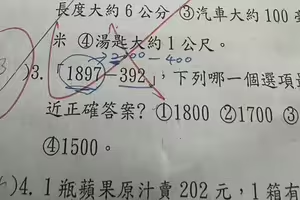兒時的記憶中,爸爸是個少言寡語的人,極少能表達出對我的愛。即使表達,他也用含蓄的方式。比如,他會將手輕輕地放在我的頭上,或用柔和的眼神久久地看著我。
10歲那年,我確信他並不愛我。一次家庭旅行時,我坐在客貨兩用車的后座上,心裡暗自打賭:如果在接下來的24小時里他能對我說點什麼,那就意味著他還愛我。但41個小時後,他才與我說話。
長大後,我遠離家鄉去上大學,畢業後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但最終我帶著妻兒又回到了洛杉磯。爸爸與我見了面偶爾也會說話,但往往只是我與媽媽要長時間談心的序曲。我知道,我們之間永遠隔著一堵沉默之牆。
後來,媽媽突然給我打電話,說爸爸摔傷了,正在醫院治療。爸爸曾經歷過兩次心臟搭橋手術,第一次動手術時我才16歲。我一度認為他也許年紀輕輕就會因心臟病撒手人寰,但這次的診斷結果卻令我毫無思想準備:他得的竟是變異性老年痴呆症。只是,誰能想到,這個病改變了爸爸,它令他不再感到壓抑,甚至擊倒了我們之間的沉默之牆。
事情發生在6個月後的一個春日,那時他正準備做膝蓋手術。我決定帶5歲的兒子傑西去看望他。我們坐在室外寒冷且背陰的平台上,爸爸披一件舊羊毛衫,心無旁騖地看著我與傑西。我與爸爸閑聊著,兒子像攀登架上的小猴子一樣在我身上爬來爬去。爸爸的眼睛睜得很大,細細觀察著我與兒子共享的自然流露出的愛意。
那天晚些時候,妻子來了。她照看著兒子,並鼓勵我與爸爸單獨待一會兒。起初,坐在病房中,我們還是一如繼往地沉默。後來,令我驚訝的是,他竟開始與我談心。
「你知道,我在外面時一直看著你與傑西。」
我用力點了點頭。他似乎在竭力搜尋著心底的往事。然後,他直直地盯著我,一雙烏黑的眼睛閃著光芒。他開始變得語無倫次,說的話比我以前聽到的要多得多。漸漸地,更加雜亂無章,我都無法重述。
但大意是:「看到傑西令我想起了……許久以前的事。在我的腦海中,是那樣久遠的事了,但我對他的印象依然如此清晰——哦,是對你的印象。當時,你是一個可愛的小男孩。」
他邊說邊笑,眼睛閃閃發亮。
「看到他……哦,是你。」他停頓了一下,「令我想起我有多愛你,只是我從未讓你看出我對你的感情。但我的確愛你,很愛你……很愛,事實上這都令我感到害怕。」
我被弄糊塗了。為何愛我會令他感到害怕?
他輕輕點了點頭,似乎理解了我的心思:「的確如此。這令我害怕。我害怕也許你與我的關係太親密了……然後,我一旦離世,你就會……被拋棄,從此孤獨。」
我陷入沉思,回想爸爸曾說過的一段痛苦的記憶。爸爸16歲時爺爺就去世了,留下他獨自承擔起照顧媽媽及妹妹的責任。當時,爺爺大概是患有躁狂抑鬱症,而且已陷入某種危境,他告訴爸爸打算結束自己的生命。爸爸十分驚恐,懇求他不要那樣做。爸爸又懇求他的媽媽,懇求他們的拉比(猶太教教士),懇求其他人勸勸他爸爸,但誰也幫不了他。一周後,爺爺開槍自殺。猶太社區不允許爺爺被安葬在猶太公墓,並故意疏遠爸爸一家人。爸爸羞愧難當,決然地帶著媽媽及妹妹搬出了猶太社區,前往加州定居。從那時起,他就將自己封閉起來,活在了沉默的面紗之後。
剎那間我明白了:原來,他的沉默竟是一個「羅生門」。於我而言,他的沉默意味著他並不愛我。但於他而言,沉默卻是能保護我、使我不歷經他曾遭受過的那種苦難的唯一方式。
我抬起頭,忽然看到爸爸的眼皮很沉重。我想他肯定很疲憊了,於是起身告別,但他抬手示意還有話要說:「我知道自己得了這個病,令我很難再思索、再回憶起我們之間的過往。」他的聲音很輕,彷彿是自言自語,「但你知道嗎?我要感謝這個病呢。若不是它,我想我們沒有機會敞開心扉談起這些往事。」過了一會兒,他輕輕叩了叩心口,「我愛你。」
說過那番話,爸爸的唇角猶自帶著一絲微笑。他慢慢閉上眼睛,再次沉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