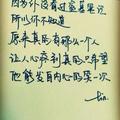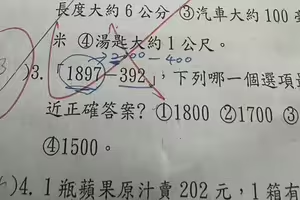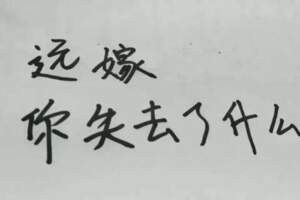那年,記得是深秋,父親搭車進城來看我們,帶來了田裡新收的大米和一袋麵條。「沒上農藥化肥,專門留了二分地給自己種的,只用農家肥,無污染,保證綠色環保有機,讓孫女吃些,好長身體。」父親放下糧袋,笑著說。我掂量了一下,大米有50來斤,麵條有30多斤。鼓鼓囊囊兩大麻袋,不知他老人家一路怎麼顛簸過來的。老家到這個城市有近100里路,父親也是快80歲的老人了。看著父親一頭的白髮和駝下去的脊背,我沒有說什麼,心裡一陣陣溫熱和酸楚。
父親看著我們剛剛入住的新房,牆壁雪白,地板光潔,「這輩子當你的爹,我不及格,沒有為你們墊個家底。你們家裡,連一片磚我都沒有為你們添過,也沒有操一點心,也沒幫過一文錢,我真的不好意思。只要你們安然、安分,我就心寬了。」我不住地說:爹你老人家還說這話,我們長這麼大就是你的恩情,你身體不錯好好活著就是我們的福分,別的,你就別想多了。
父親忽然記起了什麼,說:嘿,你看,人老了忘性大,鞋子里有東西老是硌腳。昨天黃昏在後山坡地里搬包穀,又到林子里為你受涼的老娘扯了一把柴胡和麥冬,樹葉啦,沙土啦,鞋子都快給灌滿了,當時沒抖乾淨,衣服上頭髮上粘了些野絮草籽,也沒來得及理個髮,換身像樣的衣服,就這麼著慌慌來了。走,孫女兒,帶我下樓抖抖鞋子,幫我拍拍衣服上的塵土。我說,就在屋裡抖一下,怕啥,何必下樓。父親執意下樓,說新屋子要愛惜,不要弄髒了。
樓下靠牆的地方,有一小片長方形空地,還沒有被水泥封死。父親就在空地邊,坐在我從樓上拿下來的小凳子上,脫了鞋子仔細抖,又低下身子讓孫女兒拍了衣服,清理了頭髮。上樓來,我幫父親用梳子梳了頭髮,這是我唯一的一次為他梳頭。我看清了這滿頭的白髮,真有點觸目驚心,但我又怎能看清,白髮後面積壓了多少歲月的風霜?
第二年春天,樓下那片空地上,長出了院子里往年沒有見過的東西,車前子、野茅草、蓑草、野薄荷、柴胡、燈芯草、野蕨秧、野刺玫,在樓房轉角的西側,還長出一苗野百合。大家都感到驚奇,有個上中學的孩子開玩笑說,這不就是個百草園嗎?
大家都說,新鮮,真新鮮。也有人說這個院子向陽,有空地就不愁不長苗苗草草。議論一陣也就不再管這事了。
只有我明白這些花草的來歷。它們來自父親,來自父親的頭髮、衣服和鞋子,來自父親的山野。
是的,父親也許沒有帶給我們什麼財富、權力和任何世俗的尊榮,清貧的父親唯一擁有的就是他的清貧。清貧,這是父親的命運,也是他的美德。但是,比起他的沒有留下什麼,父親更沒有帶走什麼,連一片草葉、一片雲絮都沒有帶走。他沒有帶走的一切,就是他留下的。
連我對他的感念和心疼,他也沒有帶走,全都留在了我的心裡。這麼說來,我的所謂的感念和心疼,說到底還是我從父親那裡收穫的一份感情,直到他不在了,我仍然在他那裡持續收穫著這種感情。而他依然一無所有地在另一個世界孤獨遠行。
是的,他沒有帶走的一切,就是他留下的。我看著大地上的一切,全是一代代清貧的父親們留給我們的啊。
何況,我的父親曾經把他的山野、他的草木、他的氣息都留給我們。
他清貧的生命,又是那般豐盛和富有,超過一切帝王和富翁。在他的衣服上拍一下,鞋子里抖一下,就抖出一片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