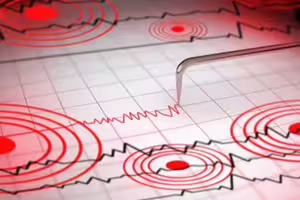1
陳子墨不是我喜歡的那種男生。
我喜歡的男生,眉毛粗糙,皮膚黝黑,背心短褲上有隱約的汗漬,是球場上歡騰雀躍的渾小子。而陳子墨,五官細緻,戴金絲眼鏡,指甲容不得半點兒灰塵,是校園裡白衣飄飄的優雅少年。
陳子墨也是不喜歡我的吧。每次途經操場,見我為體育系男友大呼小叫,他好看的長眉毛就會擰在一起,厭惡之情不言而喻。又或者,在路上,我與男友十指相扣,主動跟他打招呼,他卻懶得搭話,只是微微點頭,傲慢得好似王子接見草民的樣子。我生氣地想,要不是考試前須要參考你的筆記,我才不會理你呢。
那時,我們在一所理工大學學會計。對於專業課,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心不在焉,都以為自己出類拔萃,學了會計,像螞蟻一樣毫無創見地搬運數字,實在是沒什麼出息。所以,千方百計地逃課,去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有人考托福,有人考駕照,還有人,比如我,依靠看言情小說打發時日。只有陳子墨,聽課、記筆記,樣樣認真,把大片光陰留在了教室和圖書館裡。他抱著厚似磚頭的參考書,不分晨昏地看,那勁頭很容易讓人想起漸行漸遠的高考備戰。他慢聲慢語地跟人說,他要考註冊會計師。
平日里,好學生陳子墨和大家相處寡淡,可只要臨近考試,就有很多人找他套近乎,因為,誰都想拿到他條理清晰的課堂筆記,每次,第一個將筆記拿到手的,都是不擅長套近乎的我。我與陳子墨都來自南方的一座梅雨小城,他一直叫我老鄉。
事實上,很多女生對他著迷,可陳子墨同學對風花雪月並不感冒,他用會計理論算了一筆賬:交個女朋友,請吃飯,買禮物,陪她逛街,哄她高興,四年下來,直接成本間接成本最少要有兩萬塊,機會成本呢,那就更大了,假如我耗費大量時間談情說愛,那就可能導致考不上註冊會計師,以後按每個月少掙兩千塊,工作三十年,保守估計就是七十二萬塊啊。
陳子墨的這番高論,將那些原本對他有好感的女生嚇得掉頭就跑。誰願意跟一個天天計算感情成本的小會計談戀愛呢。
2
四年時間白駒過隙,一畢業,陳子墨和我們的境遇就大不相同了。我們手忙腳亂在人才市場分發簡歷時,陳子墨握著註冊會計師證書,從從容容和一家知名會計師事務所簽了約。我們在為房租漲價工資不發愁眉不展時,陳子墨因為業績可觀在公司得到重用,提成和獎金多得讓我們高山仰止。
時不時地,陳子墨會給我發簡訊,問,老鄉,你好嗎?我答,好。除此,再不多言。我是個內心敏感的女孩子,不喜歡在別人的錦緞上添花,也不喜歡將自己的破衣襤褸展現給那些穿了華服的人看。我與陳子墨畢竟不是一條路上的人。其實,我過得一點兒都不好,我和男友為了愛情選擇留居,像兩隻寒號鳥,笨手笨腳,哆哆嗦嗦地在這個城市裡壘窩。因為貧賤,我們爭吵,相互傷害,並感到事事悲哀,這些,我從不對別人講。
終於,再一次爭執之後,男友摔了杯子砸了鏡子,揚長而去,他的父母早已為他鋪好了去韓國的路。站在一地碎片中間,我茫然發獃,陳子墨的簡訊就在那時來了,還是那句話,老鄉,你好嗎?我不好,一點兒都不好。回信息時,我的淚大滴大滴落在手機屏幕上。十分鐘後,陳子墨趕過來,拉起我的手就往外走。因為激動,他白皙的臉漲得通紅,他第一次當面喊我的名字:「小艾,忘記過去的一切,忘記那個不能給你幸福的混蛋男人。」我就那樣,木偶一般,被他塞進計程車,跟他上樓,被他推進一間有落地窗的大卧室。他說:「以後,你住這裡,我住客廳。」卧室朝南,灑滿了陽光,銀白的紗簾在暖風裡輕輕擺動,我揉揉眼睛,淚水已經幹了,原來愛和傷痛都沒有想像中那樣轟轟烈烈。
我漸漸發現了陳子墨的諸多優點,他生活有條理、愛乾淨,還能做一手好菜。尤其是廚藝,真的是「點菜成金」,那些面目普通的蔬菜,被他掌控著在油鹽醬醋里打個滾,便脫胎換骨,成就一桌活色生香的佳肴。大約是在我住進來一個月之後吧,系著白圍裙的陳子墨,在烹調間隙,回頭說:「小艾,你要麼學會做菜,要麼找個會做菜的男人,這輩子不能虧了自己的胃。」我說:「聽起來後者更容易操作。」他紅了臉說:「你看我行嗎?」就這樣,陳子墨籠絡了我的胃,又籠絡了我的心。
確定戀愛關係後,陳子墨將一個嶄新的賬簿攤在我面前,說:「這是我工作半年來的收支情況,既然是一家人,那就用一個賬簿,以後你的收支也要入賬,我每個月做一次匯總。」翻著那本中規中矩的流水賬,我的嘴巴張成半圓,半天才合上,我說:「買一支筆你也要記上啊?」陳子墨說:「有借必有貸,發生了就得記上。」
我終於明白,做會計師陳子墨的女朋友,就得接受他精打細算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