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學——白楊樹的湖中倒影
讓人頓悟“美”
在台灣,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講。今天之所以願意來跟法學院的同學談談人文素養的必要。人文是什麼呢?我們可以暫時接受一個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個大方向。
先談談文學,指的是最廣義的文學,包括文學、藝術、美學,廣義的美學。為什麼需要文學?了解文學、接近文學,對我們形成價值判斷有什麼關系?如果說,文學有一百種所謂“功能”,而我必須選擇一種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個很精確的說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
在我自己的體認中,這就是文學跟藝術的最重要、最實質、最核心的一個作用。我不知道你們這一代人熟不熟悉魯迅的小說?他的作品對我們這一代人是禁書。沒有讀過魯迅的請舉一下手?(約有一半人舉手)
魯迅的短篇《藥》寫的是一戶人家的孩子生了癆病。民間的迷信是,饅頭沾了鮮血給孩子吃,他的病就會好。或者說《祝福》裡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個嘮嘮叨叨的近乎瘋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給狼叼走了。
讓我們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魯迅所描寫的那個村子裡頭的人,那麼我們看見的,理解的,會是什麼呢?祥林嫂,不過就是一個讓我們視而不見或者繞道而行的瘋子。
而在《藥》裡,我們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買饅頭,等看人砍頭的父親或母親,就等著要把那個饅頭泡在血裡,來養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們就是那小村子裡頭最大的知識分子,一個口齒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對農民的迷信,表達一點不滿。
但是透過作家的眼光,我們和村子裡的人生就有了藝術的距離。在《藥》裡頭,你不僅只看見愚昧,你同時也看見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狀態,看見人的生存狀態中,不可動搖的無可奈何與悲傷。在《祝福》裡頭,你不僅只看見貧窮粗鄙,你同時看見貧窮下面,“人”作為一種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
文學,使你“看見”。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種吧!壞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偉大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的同時,認出自己的原型,而湧出最深刻的悲憫。這是三個不同層次。
文學與藝術,使我們看見現實背面更貼近生存本質的一種現實,在這種現實裡,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還有直覺的對“美”的頓悟。美,也是更貼近生存本質的一種現實。
假想有一個湖,湖裡當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楊樹,這一排白楊樹當然是實體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覺到它樹乾的凹凸的質地。這就是我們平常理性的現實的世界,但事實上有另外一個世界,我們不稱它為“實”,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
水邊的白楊樹,不可能沒有倒影,只要白楊樹長在水邊就有倒影。而這個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樹干,而且它那麼虛幻無常:風吹起的時候,或者今天有雲,下小雨,或者滿月的月光浮動,或者水波如鏡面,而使得白楊樹的倒影永遠以不同的形狀,不同的深淺,不同的質感出現,它是破碎的,它是迴旋的,它是若有若無的。
但是你說,到底岸上的白楊樹才是唯一的現實,還是水裡的白楊樹,才是唯一的現實?然而在生活裡,我們通常只活在一個現實裡頭,就是岸上的白楊樹那個層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層面,而往往忽略了水裡頭那個“空”的,那個隨時千變萬化的,那個與我們的心靈直接觀照的倒影的層面。
文學,只不過就是提醒我們:除了岸上的白楊樹外,有另外一個世界可能更真實存在,就是湖水裡頭那白楊樹的倒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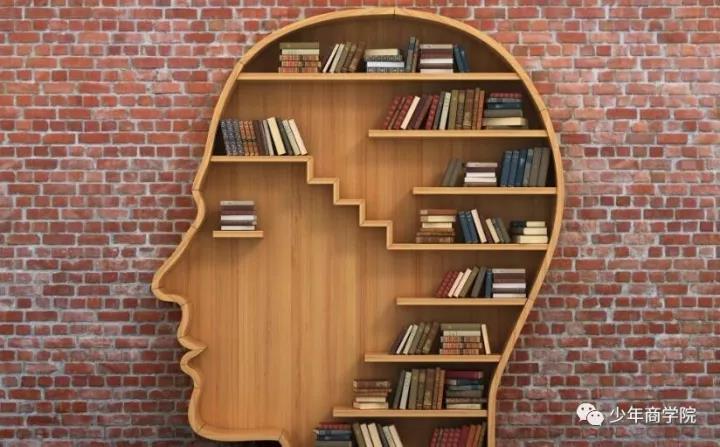
哲學——迷宮中望見星光
讓人學會發問
哲學是什麼?我們為什麼需要哲學?
歐洲有一種迷宮,是用樹籬圍成的,非常復雜,你進去了就走不出來。不久前,我還帶著我的兩個孩子在巴黎迪士尼樂園裡走那麼一個迷宮,進去之後,足足有半個小時出不來,但是兩個孩子倒是有一種奇怪的動物本能,不知怎麼的就出去了,站在高處看著媽媽在裡頭轉,就是轉不出去。
我們每個人的人生處境,當然是一個迷宮,充滿了迷惘和彷徨,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出路何在。我們所處的社會,尤其是“解嚴”後的台灣,價值顛倒混亂,何嘗不是處在一個歷史的迷宮裡,每一條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裡。
就我個人體認而言,哲學就是,我在綠色的迷宮裡找不到出路的時候,晚上降臨,星星出來了,我從迷宮裡抬頭望上看,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斗;哲學,就是對於星斗的認識,如果你認識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宮,不為眼前障礙所惑,哲學就是你望著星空所發出來的天問。
掌有權力的人,和我們一樣在迷宮裡頭行走,但是權力很容易使他以為自己有能力選擇自己的路,而且還要帶領群眾往前走,而事實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麼方位,也不知道這個方位在大格局裡有什麼意義;他既不清楚來的走的是哪條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裡去;他既未發覺自己深處迷宮中,更沒發覺,頭上就有縱橫的星圖。
這樣的人,要來領導我們的社會,實在令人害怕。其實,所謂走出思想的迷宮,走出歷史的迷宮,在西方的歷史裡頭,已經有特定的名詞,譬如說,“啟蒙”,十八世紀的啟蒙。所謂啟蒙,不過就是在綠色的迷宮裡頭,發覺星空的存在,發出天問,思索出路、走出去。對於我,這就是啟蒙。
所以,如果說文學使我們看見水裡白楊樹倒影,那麼哲學,使我們能藉著星光的照亮,摸索著走出迷宮。

歷史——沙漠玫瑰的開放
使人的眼界升級
我把史學放在最後。歷史對於價值判斷的影響,好像非常清楚。鑑往知來,認識過去才能以測未來,這話都已經說爛了。我不太用成語,所以試試另外一個說法。
一個朋友從以色列來,給我帶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裡沒有玻瑰,但是這個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裡,是一蓬乾草,枯萎的、乾的、死掉的草,這樣一把,很難看。
但是他要我看說明書。說明書告訴我,這個沙漠玫瑰其實是一種地衣,針葉型,有點像松枝的形狀。你把它整個泡在水裡,第八天它會完全復活,把水拿掉的話,它又會漸漸幹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個一年兩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裡,它又會復活。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這個團枯乾的草,用一個大玻璃碗盛著,注滿了清水,放在那兒。從那一天開始,我跟我兩個寶貝兒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麼樣了。
第一天去看它,沒有動靜,還是一把枯草浸在水裡頭,第二天去看的時候發現,它有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已經從裡頭往外頭,稍稍舒展鬆了,而且有一點綠的感覺,還不是顏色。
第三天再去看,那個綠的模糊的感覺已經實實在在是一種綠的顏色,松枝的綠色,散發出潮濕青苔的氣味,雖然邊緣還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張開,已經讓我們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圖案。
每一天,它核心的綠意就往外擴展一寸。我們每天給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個綠色已經漸漸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層層舒展開來。
第八天,當我們去看沙漠玫瑰的時候,剛好我們鄰居也在,他就跟著我們一起到廚房裡去看。這一天,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完整的、豐潤飽滿、復活了的沙漠玫瑰!我們三個瘋狂大叫出聲,因為太快樂了,我們看到一朵盡情開放的濃綠的沙漠玫瑰。
這個鄰居在旁邊很奇怪地說,“這一把雜草,你們幹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說,地衣再美,美到哪裡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難看、氣味潮濕的低等植物,擱在一個大碗裡;也就是說,他看到的是現象的本身定在那一個時刻,是孤立的,而我們所看到的是現象和現象背後,一點一滴的線索,輾轉曲折、千絲萬縷的來歷。
於是,這個東西在我們的價值判斷裡,它的美是驚天動地的,它的復活過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驚駭演出。我們能夠對它欣賞,只有一個原因——我們知道它的起點在哪裡。知不知道這個起點,就形成我們和鄰居之間價值判斷的南轅北轍。
不必說鑑往知來,我只想告訴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罷了。對於任何東西、現象、目題、人、事件、如果不認識它的過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現在到底代表什麼意義?不理解它的現在,又何從判斷它的未來?

對於歷史我是一個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學生。四十歲之後,才發覺自己的不足。寫“野火”的時候,我只看孤立的現象,就是說,沙漠玫瑰放在這裡,很醜,我要改變你,因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
四十歲之後,發現了歷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麼過來的,我的興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評,而在於:你給我一個東西、一個事件、一個現象,我希望知道這個事件在更大的坐標裡頭,橫的跟縱的,它到底是在哪一個位置上,在我不知道這個橫的跟縱的坐標之前,對不起,我不敢對這個事情批判。
了解這一點之後,對這個社會的教育系統和傳播媒體所給你的許許多多所謂的知識,你發現,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從小就認為所謂西方文化就是開放的、民主的、講究個人價值反抗權威的文化,都說西方是自由主義的文化。用自己的腦子去研究一下歐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驚:哪有這回事啊?西方文藝復興之前是一回事,文藝復興之後是一回事;啟蒙主義之前是一回事,啟蒙主義之後又是一回事。
然後你也相信過“中國兩千年專制”——你用自己的腦子研究一下中國歷史就發現,咦,這也是一個半真半假的陳述。
中國是專制的嗎?朱元璋之前的中國,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國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國,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國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麼你說“中國兩千年專制”,指的是那一段呢?
這樣的一個斬釘截鐵的陳述有什麼意義呢?自己進入歷史之後,你納悶:為什麼這個社會給了你那麼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訴你這些是半真半假的東西?
對歷史的探索勢必要迫使你回頭去重讀原典,用你現在比較成熟的、參考系比較廣闊的眼光。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過的路,但是對於過去的路有所認識,至少是一個追求。重讀原典使我對自己變得苛刻起來。
有一個大陸作家在歐洲某個國家的餐廳吃飯,一群朋友高高興興地吃飯,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離開餐館很遠了,服務生追出來說:“對不起,你們忘了付帳。”作家就寫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贊美歐洲人民族性多麼的淳厚,沒有人懷疑他們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們中國的話,吃飯忘了付錢人家可能要拿著菜刀出來追你的。
我寫了篇文章帶點反駁的意思,就是說,對不起,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異的問題。這恐怕根本還是一個經濟問題。比如說如果作家去的歐洲正好是二次大戰後糧食嚴重不足的德國,德國待者恐怕也要拿著菜刀追出來的。這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體制結構的問題。
寫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覺得自己很有見解。好了,有一天重讀原典的時候,翻到一個暢銷作家兩千多年前寫的文章,讓我差點從椅子上一跤摔下來。我發現,我的“了不起”的見解,人家兩千年前就寫過了,而且寫得比我還好——韓非子的《五蠹篇》。
韓非子要解釋的是:我們中國人老是贊美堯舜禪讓是一個多麼道德高尚的一個事情,但是堯舜“王天下”的時候,他們住的是茅屋,他們穿的是粗布衣服,他們吃的東西也很差,也就是說,他們的享受跟最低級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當國王的時候,他的勞苦跟“臣虜之勞”也差不多。
所以,堯舜禹做政治領導人的時候,他們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層的老百姓差別不大,“以是言之”,那個時候他們很容易禪讓,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能享受的東西很少,放棄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今之縣令”——在今天的體制裡,僅只是一個縣令,跟老百姓比起來,他享受的權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紀的語言來說,他有種種“官本位”所賦以的特權,他有終身俸、住房優惠、出國考察金、醫療保險……因為權力帶來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個家族都要享受這個好處,誰肯讓呢?
“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麼呢?“薄厚之實異也”,實際利益,經濟問題,體制結構,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樣的行為。
看了韓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兩千年之後,你還在寫一樣的東西,而且自以為見解獨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這種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認為其實應該是一個基本條件。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過的路,但是對於過去的路有所認識,至少是一個追求。
講到這裡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學評論,談個人才氣與傳統,強調的也是:每一個個人創作成就必須放在文學譜系裡去評斷才有意義。譜系,就是歷史。
文學、哲學跟史學。文學讓你看見水裡白楊樹的倒影,哲學使你從思想的迷宮裡認識星星,從而有了走出迷宮的可能;那麼歷史就是讓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點,沒有一個現象是孤立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