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61歲的蔡明亮完成新片《你的臉》,
這部作品77分鐘,全程只拍攝了13張臉,
入圍威尼斯電影節,受邀40多個影展,
是去年台灣金馬獎閉幕片。

13張臉中,有一張是他27年來的御用男主角——李康生,
他們一起拍了十多部電影,
每一部蔡明亮的電影裡都有李康生,
“他的臉就是我的電影,
他不在的話,我都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拍電影。”
今年5月17日,《你的臉》將於在台北光點華山電影館獨家上映,
電影預售票同步於台北光點華山電影館搶先販售。
我們去蔡明亮的家拜訪了他,
也見到了李康生,
聽蔡明亮聊他的作品,
以及他和李康生一起度過的電影人生。
【電影大師蔡明亮】


見到蔡明亮的時候,他正在新北的家中煮咖啡,
落地窗面對一片山谷,有兩隻野貓在院子裡溜達。
他和李康生一起打理這個院子,種了桃樹、松樹、野柚子。
房子原本是廢墟,改造以後才能住人。
鄰裡還是廢墟,沒有人住。
蔡明亮常常去隔壁散步,一間間廢棄的房子,裡面長出了各種植物,
斑駁的牆壁,生出了各種顏色的真菌。
兩年前,他曾以這片廢墟為取景地,拍了《家在蘭若寺》。


家中一樓堆放著電影膠片的拷貝,牆角的3層小櫃子上放著各種形狀的獎盃。
掃了一眼,看見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銀獅,柏林電影節的熊,還有幾個金馬獎。
從第一部電影《青少年哪吒》開始,他幾乎每部作品都會收穫國際電影節獎項。
大約和搬來這裡同一時間,他的作品開始走進美術館,暫時離開電影院。
創作也越來越自由,甚至早年作品的痕跡都不見了,
就只拍李康生用極慢的速度行走,或者像《你的臉》凝視一張張臉。


隔壁就是《家在蘭若寺》的取景地
這裡是他的家,也是工作室,還是咖啡館。
他和李康生、陸靜奕合開的蔡李陸咖啡館,在中山堂租約到期之後,就搬來了這裡。
帶我們來的計程車司機一聽地點就知道:“哦,那個賣咖啡的導演。”
他曾經說過,自己這輩子為什麼敢賣電影票和賣咖啡:
因為我的電影好看,我的咖啡好喝。
以下是蔡明亮導演的自述:


我的鏡頭下,你的臉
我喜歡拍臉。
2009年我為法國羅浮宮拍了一部電影, 片名就叫《臉》。
《你的臉》是去年完成的新作,它沒有劇情,沒有故事,
只有13張臉坐在我的鏡頭前給我拍攝,全片77分鐘,一共14個鏡頭。
13張臉除了李康生,另外12張都是在街頭找的素人,找的時候並沒有限定年齡,
最後找到的都是從60多歲一直到80多歲,有一點歲月的面孔。

有一個賣香煙的老太太,戴一串項鍊,牙齒都沒有了,戴一個假牙。
她也不是為生活所迫,因為她先生已經不在了,
在家裡就會想先生,所以她就每天要出來跟客人見面。

85歲的馬先生
有一個85歲的馬先生,一經過他,我就被吸引住了,
他高高瘦瘦,有一點結實,臉是佈滿皺紋,那個皺紋很深邃。
他八十多歲還在幫忙家裡的小店做便當、炒菜,
子女們讓他不要工作了,他非要出來,在家裡待不住。
他們都還在很認真地生活,我就會被這種還在“活著”的臉吸引,
找的時候不知道他們的故事,看到臉就想拍了。

他們都不是演員,我也不打算做訪談,拍成紀錄片。
我只是讓這些伯伯、奶奶坐到我的鏡頭前面來,什麼都不做,
其實是一個很奇怪、也很不容易的工程。
每個人會拍兩遍,每次是25分鐘,我跟他們說,請忍耐一下。
第一遍是閒聊,讓他們放鬆。
再來一遍就是不說話的,一直看著鏡頭。

有一個老先生,第一遍拍的時候,我們聊得很熱絡,
他以前跟黑道很熟,講那種小流氓、大流氓打架的故事,
跟竹聯幫怎樣怎樣,講得特別精彩。
第二遍拍的時候,他兩分鐘就睡著了。
我覺得特別好,講話的內容我沒有留在影片裡,他睡著比他講得還好。
這個作品的整個意思就是讓你來觀看一個影像,凝視一張老人的臉,你會有什麼感覺?
你可能會想到很多,想到時間、媽媽,想到自己也會老。

我們很怕看一個東西看太久。
生活裡,我們也不會這樣一直盯著一張臉看,再愛他也不會。
甚至有時候反而會逃避,你知道,這就是人嘛。
我自己的人生經驗裡面,我有機會這樣子去凝視一張臉,大概就是我媽媽過世前。
有兩個小時我一直盯著她,盯著那張臉,看她彌留的狀態,呼吸的改變。
原來,人的呼吸是這樣子的,所以什麼叫“生命如燈”,
那個油被燒盡了,它不是馬上就沒有了,
它是很慢、很慢、很慢,生命像一陣煙一樣飄掉了。
我外甥女很小,她說:“奶奶睡著了。”

所以說為什麼要有電影的發明?就是要讓你看。
一定要有個人先看到,他才能讓其他的人都看到。
我覺得這個時候緩慢電影的價值也許就跑出來了。
它給你這個機會,用十分鐘去肆無忌憚、毫無保留地看一張臉,
不用害羞,也不用擔心對方的目光。
需要一個比較慢的速度讓我們看到時間。

《郊遊》劇照。
李康生憑藉《郊遊》獲第50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
獲獎致詞前,他把獎盃舉起,定格了好幾秒鐘,
然後說“這不是電視機壞掉,是蔡導拍片的風格” 。
從電視劇編劇到“緩慢電影”作者
我是一個叛逆的小孩,不是行為上的叛逆,在心裡面叛逆。
我在馬來西亞長大,少年時覺得家庭捆綁我,我就要離開家。
大學來到台灣。
來台灣之前,我父親跟我說,你來台灣我最放心,
因為當時台灣是軍政時期,非常嚴格,不能留長頭髮,有些歌也不能唱。
可是我才來不到兩年就解嚴了,所有東西都湧進來,
我親眼看到台灣從軍政時代變成一個自由時代。
在一個不被限制的環境裡,我開始了自己的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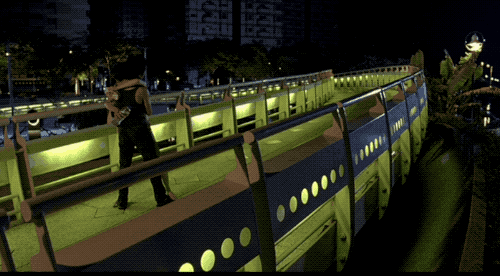
蔡明亮2005年電影《天邊一朵雲》的經典長鏡頭
一開始我是寫劇本,也看台灣“新浪潮”那一批導演的作品。
我特別喜歡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楊德昌的《海灘的一天》,
包括王童的《看海的日子》,張毅的《我這樣過了一生》。
看得很大量、很密集。
到後期我自己被撼動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歐洲的。
很多電影印像很深的都是鏡頭特別長,很慢,對話也少。
出來以後我就跟朋友討論:“那個畫面那麼長,那麼不講話,那個編劇怎麼寫?”
我是站在編劇的立場思考:編劇要怎麼寫?那個導演可以這樣拍?
因為我做編劇的時候,我的導演其實都很欣賞我,
我自己練習寫出一個畫面,不需要使用鏡頭淡入、淡出這些術語,
用文筆寫到他好像看到這是一個特寫,這是一個推拉鏡頭。
很多導演拿到我的劇本覺得不用費心,就可以拍。

《不散》中的李康生
我大學念的是戲劇系,西方戲劇很講究結構。
我們大量地閱讀莎士比亞,講三一律,讀戲劇原理。
做電視編劇以後,我慢慢地開始懷疑、厭惡“編”這個事情。
我常常問自己:“電影是劇本嗎?劇本是電影嗎?”
畢業後十年,有機會拍自己的電影。
拍《愛情萬歲》(1994)的時候,工作人員不知道我在拍什麼,
因為拍了3個星期,沒有一句台詞。
台詞越來越少,《不散》(2003)全片82分鐘,只有10句台詞。
劇本就是兩頁的稿子,寫了大概二三十行詩,類似詩的句子,
“下雨啊……”“戲院,有隻貓走過”。
電影是影像有力量,而不是故事有力量。

《不散》劇照。
影片中,蔡明亮對著空蕩的戲院座椅拍了5分鐘
《不散》有一個很常被討論的畫面,就是那個椅子5分鐘不動,沒有人的。
我記得我的剪接師勸我:“不要啦!”
錄音師也說:“不要!那麼長,觀眾會瘋掉。”
我就是偏要。
這部片子後來得了金馬獎的最佳剪輯獎。
它在威尼斯競賽的時候,一位50多歲的法國記者告訴我,
這十幾年來,她看電影都有一個感覺,
好像在閱讀的時候,有一隻無形的手在幫她翻頁。
但是看我的電影,因為每個鏡頭都很長,
她可以自己去看到細節,聽到聲音,產生感覺,然後去思考。


《河流》劇照
我要找到我的自由,因此,我可以在我創作的電影脈絡裡講很私人的事情。
我的作品大概都在呈現解困的過程,每件作品都在處理“如何逃開各種捆綁”,
包括道德、現實、社會,或者個人內在的陰暗面。
拍《河流》(1997),得罪了男人,也得罪了女人,
大家都在罵,票房也很差,我那時候已經是被打擊到不行了。
我的一位恩師有天就約我出來說,
阿亮,你告訴我為什麼要這樣拍一對父子,有沒有別的方式,
我相信你那麼聰明,應該有辦法用另外一種方式處理吧?
我被他一問,我真的思考了,思考了兩分鐘,我們就靜默了兩分鐘,
我就說,沒有,我只會這樣拍。
我的老師就很用力地拍我的肩膀,他說,
這就是你啊!你不是別人啊!你要珍惜你這樣的能力。我就走下去了。
李康生有個特質很能引起我的共鳴。
這個特質叫“反叛”,他不愛說話,動作比常人慢一拍,
他不太在乎這個世界的速度,不太在乎這個行業的規矩。
他也完全不符合電影這個行業既有的規範,高大、漂亮、會演戲、有節奏感等,
後來我幾乎是跟著他的節奏、速度、個性和不說話這個特質來創作。
我也脫離了這個行業的束縛。

李康生是老天這輩子給我最大的禮物
李康生的臉就是我的電影。
我第一次見到李康生是二十多年前,
一個電視劇需要一個高中生壞小孩,我就在街頭遇到李康生。
他那時候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
小康演我的第一個戲,我嫌他走路像機器人,重拍二十幾次。
每回都說,再自然一點,再自然一點,幾乎快用吼的了。
他幽幽地回我一句,我就是這樣走的啊,當頭棒喝。
從遇到他開始,我開始改變。
演戲常常有一個套路,怎麼打耳光,怎麼掉眼淚,
可是他讓我意識到,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青少年哪吒》劇照,小康站在《無因的反叛》海報前
我的第一部電影《青少年哪吒》是根據他當時的狀況、他的家庭背景來寫的。
一個準備重考大學的青少年,李康生演的就是他自己。
我拍電影的時候有一個經驗很特別,打光的時候需要有替身,
因為演員要休息,所以會請劇組工作人員坐上來,讓燈光師慢慢調光。
我看著鏡頭裡的畫面,老覺得說怎麼不好看?美女來也一樣不好看,
等到演員一坐上來,蓬蓽生輝。
李康生就是這樣的一個演員。
剛開始當導演,拍了兩部片以後,就已經有人跟我講不要用李康生了,
因為他不紅,他沒有紅起來,還有更帥的人排隊在那邊要演電影。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可能是命運的安排,
我們一直有機緣往下合作,到後來我就不換他了。

《那日下午》蔡明亮對談李康生
他其實也有掙扎。
他心裡面也有一種對演員的概念:“我應該演一個黑幫的,演個殺手、英雄之類的。”
他會說:“你弄個商人給我演之類的。”
但是我的電影沒有朝那方面去思考。
後來香港也有經紀人要簽他,簽了5年。
演許鞍華的《千言萬語》(1999),我去探班,發現小康好累,
要他哭,要他用演的,那個電影是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
他那時候常跟我頂嘴說不想演我的戲,就是同志,就是那些角色。
後來那個念頭好像沒有了。
慢慢地我覺得他就安靜下來,就知道跟我在一起是在做一件事情,做創作。

《天邊一朵雲》劇照
其實我們常吵架,最嚴重的一次就是有一次我們公司被掏空了,
那時準備要拍《天邊一朵雲》(2005),被人家騙了,
那個人是我最相信的人,公司的存摺、印章全給他,當時我對人失去了信心。
然後我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們打電話,小康說不想再跟我了,
什麼都沒有了,因為媽媽的房子也被押下去了。
我那時候很傷心,他這樣說的時候,我對他吼,
我說,“我們不是什麼都沒有……我們拍了很多很棒的電影!”
我拍《河流》(1997),是因為李康生在演完《青少年哪吒》之後,
生了一個怪病,脖子往一邊歪,我在現實生活中陪他四處求醫。
看醫生的過程,對我非常有衝擊,就寫了那個劇本。
我為什麼拍《你那邊幾點》(2001),李康生的爸爸過世之後,
原本看起來就不開朗的他更加憂鬱了,怎麼能走出來呢?
我就想拍一個關於父親過世的電影。


《是夢》劇照
我生命中有三個男人超重要的,一個是我爸,
我其實不是很了解他,成長過程中並沒有跟他很接近,但是那種父子感情還是很深。
他知道我在拍電影了,可是我第一部電影在拍的時候他就過世了,
所以他沒有看過我拍的電影。
第二個是李康生,我其實是根據我爸的樣子找的李康生。
我拍過一個短片《是夢》(2007),李康生就是演我爸。
穿我爸的衣服,跟我媽在一起演出。
我媽當時已經是一個老太太了,所以說“是一個夢”。
第三個是玄奘。
我30歲出頭的時候看了他的傳記,大為感動和震撼。
我忽然發現,原來1400多年前,曾經有過一個真實的人,有過一雙腳,從西安走到印度。
沒有交通工具,沒有語言的能力,沒有各種資訊,
甚至沒有閃光燈在終點等著迎接他,只有一個人孤獨地踩上茫茫無知的道路。
我覺得玄奘去取經的時候,其實他沒有想到自己會成功,他就做了。
當然他做到了。人其實是可以不用看重目的而去做一些事情的。


《行者》系列之一,在法國馬賽拍攝的《西遊》
後來拍《行者》,覺得李康生演的就是玄奘,起碼那個精神是,
就是往前走,不知道要去哪裡,就是往前。
《行者》起因是2011年,我和李康生合作的一部舞台劇《只有你》。
有一場戲我們排了很久都排不好。
其實那場戲非常簡單,一堵牆,
李康生在那邊的時候還是自己,可是走到這邊就變成我爸爸。
這個過程到底怎麼演?
後來有一天他就跟我講,導演我想用走的,我覺得走過來就好了,
我從這邊走到那邊,就變成你爸了。
可是我說你要讓我服氣啊,你要怎麼走?
我指定了一個點到一個點,他就用很慢的速度走,走了17分鐘。
我都看呆了,非常震動,脫口而出:哎呀我等了你20年,就是等這一刻!
李康生是老天給我的了不起的禮物,他永遠能夠讓我詮釋生命的艱難。
我覺得他的走路太美了,就想拍成影像。

《行者》系列在台灣沙丘

《行者》系列在馬來西亞古晉,蔡明亮的出生地

《行者》系列在香港
五六年裡面我們拍了八個《行者》,
不同的景觀,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狀態,只有一個元素就是李康生走路。
用很漫長的速度在移動,然後讓你認真地看到這個世界。
八個《行者》就是時間,好多年的時間,好多年的李康生。
我拍到五六部的時候就開始有美術館請我去展覽,維也納、布魯塞爾、韓國。
現在是台灣東北角的遊客中心,裡面只展這八部《行者》,一直展覽兩年。

《你的臉》片段
我特別感動的是《你的臉》裡李康生說了一句話,“我也老了。”
其實拍到現在,他有掙扎我也有掙扎,
我的掙扎是希望他能像劉德華那樣愛惜自己,不變胖,
希望他還是很漂亮,慢慢地,也接受了這個事實,他也會老。
看李康生的臉變老,你不是笑他,而是覺得太珍貴了。
後來我覺得說,拍戲好像是為了他。
其實到後來我多討厭拍戲啊!
就累、懶、煩,焦慮,但是由他演,ok,我就去做了。
現在我有一種很放心很放鬆的感覺,我覺得我不用拍太多戲,
甚至我不用再拍戲了,我覺得我可能只要拍小康走路就好了。
如果他不在,我真的不太知道我為什麼要拍電影。

《郊遊》在美術館,攝影:黃宏錡

蔡明亮和美術館觀眾聊天
從電影院到美術館
我大概在幾年前,身體非常不好,就是過勞。
過勞的原因很簡單,每次我的電影上映前,其實我都要親自去街頭賣票,賣了十幾年。
我的片子雖然都得了獎,但是劇情悶,賣相不好。
我和李康生一起,走遍全台灣,一張一張地賣票,每次都是賣一萬張才打住。
一萬張票拿到電影院,老闆最少給我兩個禮拜上片。
所以後來所有的電影院的老闆都知道,只要蔡明亮上了片,都不會不賣座。
一萬張票,可能只有兩千人是想看你的電影,八千人是同情你也好,
其他原因也好,他來了看了,也許很氣地出去了,或者很感動就留住了。
這就是我面對現實的一種方式。


“夜宿沙丘”活動,觀眾帶睡袋在美術館看電影
從2013年《郊遊》開始,我逃離了電影院,去美術館。
因為美術館會簽兩三個月的約,不用擔心票房,不會下片。
但是我的個性就是,不會讓美術館空著。
所以我還是一張張賣票,去各大院校賣票,把作品跟我自己綁在一起,
辦夜宿美術館這些活動,使勁各種法寶,讓大家進美術館。

蔡明亮為“夜宿沙丘”的觀眾唱歌攝影:黃宏錡
《你的臉》最開始,其實也是一個拍給美術館的作品。
就是13張臉,誰要買票去電影院看呢?
可是我又突然回頭想說,誰規定去電影院就一定要看故事片呢?
所以我就決定要在今年把這個電影推到院線去。
《你的臉》看完我常常有一個感覺,
原來人生有時候是非常簡單的,哪裡有那麼多劇情。
愛恨情仇都是被時間拉得很長,沖得很淡。
當你到一個年齡再講的時候,都是雲淡風輕,裡面那些人講話也變得像唱歌一樣。


前幾年,我搬到這個山上來,老天給了我一個特別的禮物,
給了一個山谷一個景,可以每天對著它。
我一輩子沒有想過買房,也沒想過要固定住在一個地方,
但是我對現在住的地方有回家的感覺。
是一幢從廢墟改造出來的房子。
我自己每次看一些房子,會覺得好難看,
可是等它廢棄了,就覺得好好看,
廢棄裡面包含著時間,像皺紋、傷痕、老人斑等等。
最真實就是廢墟啊!全部東西都會變成廢墟。
住在這裡,我好像才發現我原來有這麼自由的時間,
我可以看到風在吹那些野草,看到鳥在樹上,我就覺得好幸福。
所以我常常都在表現時間,不知不覺的在影像裡面表現時間。

拍這些電影到底要幹什麼?
我後來想到了一個道理,這世界最需要做一件事情,
每個人都能做到,如果他願意的話——看天上的月亮。
如果你願意看月亮,你的心情一定每次都不同,
於是你能安靜下來,變得比較敏感一點,更柔軟一點。
我們的心都不柔軟了,只知道自己的痛,不知道別人的痛,
看我的電影是一種訓練,會看我的電影就會看月亮,
如果你常看月亮,也會看懂我的電影。



























